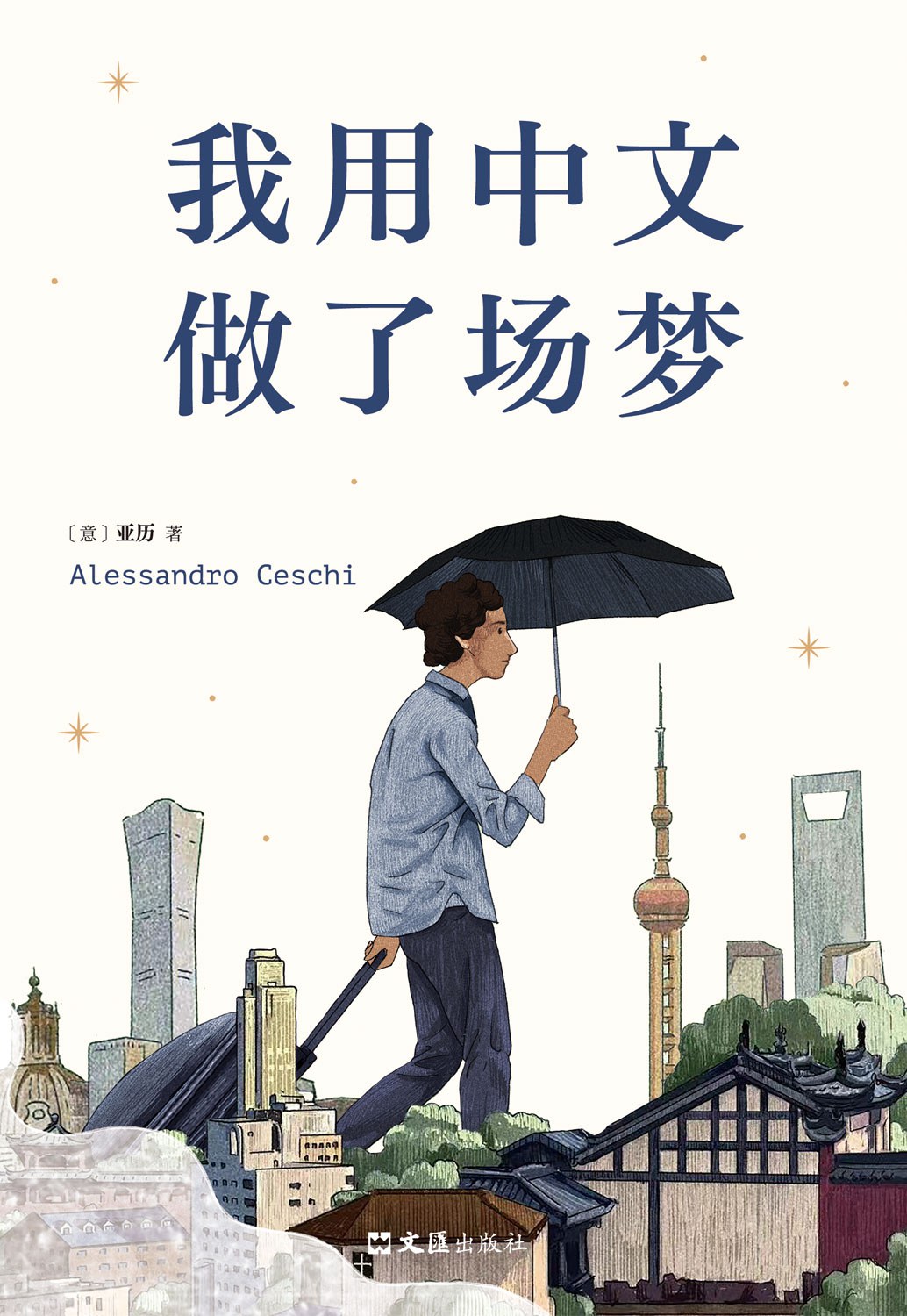评论家谢有顺自称文学基础很差。他的初中是在村里读的,条件简陋,没有英语课,没有图书室,也没有文学杂志,到县城读师范学校后,能看的杂志也不多。然而他对文学的热爱早就开始了,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探讨先锋小说的语言问题,后来又有论述先锋小说的长文发表在了《文学评论》杂志上。他大概是这份知名刊物复刊后年龄最小的作者。那年他读大学三年级。
一切恍如隔日。当年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如今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也走过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谢有顺对文学的热爱从未改变,对纯正学术的追求从未改变。在新作《文学的深意》中,他置身文学现场,思考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秉持“文学与生命互证”的价值立场,看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格张力,视野开阔而深邃,行文清醒而警觉。在谢有顺的笔下,赢博体育app文学不但事关现实、语言、想象力、技巧,更事关主体、心灵、人格和边界,因而他的文学评论是可读可感、可思可想的,更是有温度有态度、有能量有生命的。
《文学的深意》,谢有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69.00元
中华读书报:翻开《文学的深意》,你的阅读和点评纵横捭阖,既有对作家个体持续几十年的关注,也有对各路作家的横向比较,诗歌、散文、小说多种文体兼有涉及,显示了作为评论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到见识。在《个体的凝视》一章中,收入了你对韩少功、莫言、于坚、阿来等人的评论。你是如何选择评论对象的?有什么原则吗?
谢有顺:首先是要评自己喜欢的作品,不喜欢的,我沉默就是了。有些人老是苛求评论家,希望评论家对各种作品发言,这是不现实的,没有人有那么大的阅读量和写作能力,每个人都只能取一瓢饮。至于自己愿意评论的作家,也要在艺术风格和精神趣味上与自己有契合,才会有评论的冲动。很多人以为评论家只评论自己朋友和熟人的作品,错了,好的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庸俗,像书中收录的关于韩少功、阿来的评论,都是我写的第一篇评论他俩的文章,但二十多年来,我和他俩一直有良好的关系,写不写评论并不影响我与一个作家的交往,在一起聊天,有时收获更大。
我评判作品好坏的原则有三。一是它在艺术上必须有新意,是值得分析的。二是我看重一个作家的语言才能,语言的个性、韵味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风格化的重要标志。三是作家的道德勇气也不可忽视。它关乎作家是站在什么精神立场上说话,他有什么样的价值发现。这三点,常常是我要评论一部作品时的准则。而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工作者,艺术的修养、精神的敏锐和鲜明的文体意识,缺一不可。没有艺术修养,就无法准确解析作品的丰富和复杂;没有敏锐的精神触角,就无法和作家进行深层对话;没有文体意识,批评文章可能就会写成新八股文,而失去好文章应有的风采。
中华读书报:《感觉的象征世界——〈檀香刑〉之后的莫言小说》中,对《檀香刑》之后莫言的感觉方式和感觉意旨的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能否以莫言为例,谈谈你是如何展开阅读和评论的?写作中你会就某些疑问和作家交流吗?写完后会把文章发给他们征求意见吗?

谢有顺:这篇对莫言作品的评论文章是《文学评论》杂志约的稿。我本来想写三个问题的,结果第一个问题“感觉象征化”写完,已经有一万多字了,就临时改为只探讨这个问题:“感觉象征化是现代小说的重要标志。而从具象性的感觉走向象征性的感觉,更是莫言成为好作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之前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研究莫言。我对莫言的作品相当熟悉,可我读了不少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后,发现很多人都强调莫言小说的感官化描写,尤其强调他的感觉发达,小说写得色香味俱全,但没太注意到他从《檀香刑》之后把感觉象征化、具象化这一特点。于是,我就找出了从具象性的感觉走向象征性的感觉这条线索来展开论述。写文章,角度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你如何立论,有角度之后,你才能把与之相关的阅读记忆串成学术地图,进而组织成文。
我年轻的时候,文章写得快,追求气势,但思考往往不够沉实,层次感不够,文章的语言也常常处于打滑状态,难以深入探讨问题。我现在有挺大的变化,写作之前,必须大量看书,我会把与论题相关的各种书都找出来,起码几十本,快速翻读,目的不过是激活思维,未必真正引用。在快速阅读的过程中,让大脑活跃起来,抓取一些思想碎片,形成思路,从一个想法勾连起另一个想法,从一个细节联想到另一个细节,然后我会记下关键词,开始写作。我没有一篇文章是想好之后再开始写的,都是边写边调整,边写边丰富,有时想好了的,写着写着思路往另一个方向走了,那就顺着语感往前走,这种意外和旁逸斜出,往往是文章里最有光彩的部分。文章要有生气和活力,就要有流动性的想法和语感,机械的、规律式的写作方式,只是把材料和观点按几个方面归置好,未必有贯通的文气。所以,写文章不能没有准备,也不能准备得太充分,保持一点未知和随意的部分,才有创造的快乐。
我写任何文章都不会中途与作家交流,更不会把写好的文章发给他们征求意见。批评也是一种独立的写作,而写作的根基恰恰是“孤独的个人”。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个体的想象天堂”,“所有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保持个性的独立,才能训练自己锐利的发现能力。
中华读书报:《文学的深意》中的文章读后耳目一新。你的评论简洁有力,温和又不失锐气,和作家作品贴得很近,又置之度外,有清醒的判断和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你在评论作品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谢有顺: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做批评大致相似,抓住大问题、大方向,很多枝节的问题就容易洞悉和解释了。但也有不同,毕竟文学是人学,是生命的学问,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解读。因为文学作品有生命这个维度,就表明它是活泼的、动态的、变化的。要把握住文学这个动态的生命体,首先要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不仅要对作品有感觉,还要对作品中的人有感觉,对作品中的语言有感觉。没有感觉,就意味着你看什么都是僵死的,这样的人可以去做客观研究,但不适合研究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感觉的艺术。
中华读书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评论家?你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谢有顺:我希望自己是热爱文学并仍然坚守文学价值的批评家。如果要问我何以从事文学批评,我想它只能是来自于热爱。没有热爱,坚持在这条批评的小路上走下去是很难的。法国批评家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讲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而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说:“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这些都是理想的批评状态。尤其是每次读到好作品,心里总有一种感激之情,觉得要说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所读的作品。
说到文学与时代之关系,任何人的写作都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而做当代文学研究,要熟悉当代文学的现场,但也不能完全跟着热点走,现象、热点太多了,贴得太紧,太时髦,很快就会被时间所冲刷。时代滚滚的洪流中,有浮在上面的泡沫、树枝,也有沉下去的石头,我们还是要在时代的洪流中抱住石头。
中华读书报:在《如何批评,怎样说话》一文中,你提到“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批评界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你如何看待当下批评的困境?
谢有顺:过度学科化、知识化的学术趋势,损伤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直觉和感受,批评越来越成为没有体温、没有个人发现的理论说教。之前的批评,强调个人风格,强调对一部作品的艺术直觉并勇敢地做出判断,现在,这种可贵的品质正在消失。过度赞美、过度苛责甚至谩骂,都是批评家审美瘫痪的表现,批评一部作品有时是好事,但过度苛责有时就会失去公正。批评还是理性些、诚恳些好,不必那么怒气冲冲、真理在握的样子。批评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不盲从的,反奴性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它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在文学批评中,我认为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
中华读书报:你在书中提出真正的批评,要通过有效地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重申自己的存在。那么,你是如何做到“真正的批评”,如何做到“诚实于自己的恭维”“诚实于自己的揭露”?
谢有顺:法国评论家伊夫·塔迪埃认为“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确实,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洞察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如何书写一个生命世界,最终它说出个体的真理。但批评家也有自己的边界、自己的底线,要有艺术的判断力,要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过去我们以为批评的专业精神是一种学术积累,或者是阐发文学作品的能力,现在看来,这样的界定未免过于狭窄。如果我们承认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写作,那就意味着,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比任何一种批评的理论规范都显得重要。我看到了太多的批评,在对作品进行僵死的解释,并发表毫无智慧的说教,这使得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丧失了对大多数批评文字的敬意。批评并非仅是一种学术方法或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批评者要有一种卓越的精神视力,以洞见文学世界中的人心秘密——文学发乎人心,也以解释人心的秘密为旨归,学写作与学做人在精神底子上是一致的,而惟有创造出了通往人心的径直大道的文字,才是直抵根本的写作、直抵根本的学问。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发布于 2025-01-19
发布于 2025-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