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郭敬明、韩寒等青年作家以决然不同的姿态闯入年轻读者的视野,成为“80后”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作品锋芒毕露,风格多样,聚焦年轻人所关注的时髦生活,掀起一股狂热。
十几年后,这些当初备受注目的人似乎纷纷逐渐从写作转移到其他行业,只有在娱乐新闻中才能看到他们的身影,“80后”成为一个古早的名词。而在娱乐圈的聚光灯焦点之外,依然不乏笔耕不辍的“80后”写作者。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文景举办了一场名为“用写作见证一代人的成长”的对谈活动,由评论家李伟长主持,“80后”作家叶扬、陆源、周嘉宁分别讲述了自己如何开始写作,以什么样的状态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坚持。

叶扬、陆源、周嘉宁都是“80后”,他们的童年时期恰逢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的蓬勃发展,是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代。大量引进的外国小说滋润了作家们的童年,使他们积累了启蒙的阅读经验。
虽然同为“80后”,是毫无争议的“一代人”,三人进入写作的入口却截然不同。
叶扬大学念的是建筑,从BBS时代开始创作,“当时在论坛上跟人吵架,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开始写小说。”
当时文景的一位编辑看到她在BBS上发表的小说,提出可以尝试将之出版成一本书。BBS写作有个好处,能接收到读者第一时间发来的反馈。现在没有了BBS这样的互动平台,叶扬每次出书的时候最渴望的还是收到反馈,前段时间有位高中生读者通过微博私信发给她手写的8页读后感,这让她感动不已。她希望读者读完后去评价,无论是好或坏都可以,别人跟你说他理解你的故事,这会带来一种动力。
陆源是财政学专业出身,自认算不太典型的写作的人。他戏称曾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小说家”,因为他曾经认定自己在写小说之前从来没有特别想做任何别的事,走上这条道路有必然性。直到某天他忽然回忆起自己在大学时期非常渴望能做计算机方面的工作,这才意识到记忆的真实有别于客观的真实,他自己其实无意识地隐藏了自己的记忆。
作为“80”后,陆源认为这一代人与前辈相比,非常幸运的是能有机会读到众多外国文学,吸取了大量营养,“才有可能走向一条我们现在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之路。”正是因为那段“出版的黄金年代”,“80”后这一代人有机会在思想观念还未定型的阶段接触到大量优秀的文学,他和叶扬这样没有受过大学科班文学训练的理科生,才有机会摆脱命运的必然性,主动选择去做一个写作者,并在这条道路上有所成就。
与前两位嘉宾非文学的专业背景不同,周嘉宁因获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后一直从事写作。
但对于周嘉宁而言,自己的写作也并非从高中开始,在20岁末尾、30岁开头的年龄,她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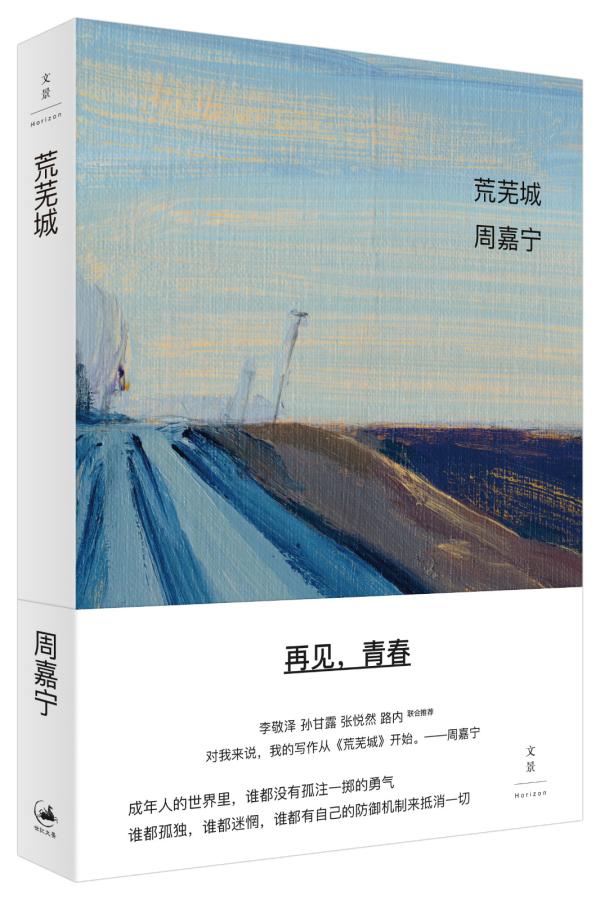
周嘉宁的小说《荒芜城》刚刚再版,尽管在《荒芜城》出版前她已经有10余年的写作经验,但她仍然将这部作品作为自己写作的起点,在她的简历上,这部小说之前她没有列上任何作品,“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写作。其实写《荒芜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写作,但我觉得我的练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在练习,如何在学习。”
与前辈相比,大量“80后”写作者并非把写作当成唯一的职业,很多写作者都有另外一份工作,在青少年时期,也都拥有迥异的人生经历。李伟长提出了一个问题,“80”后写作者脱离于写作之外的另一部分工作和生活,是否会以某种思维方式或是记忆,进入到他们的文字之中?
叶扬现在从事建筑杂志编辑的工作,她坦陈自己并未有意做这种尝试,她极少将身边的故事写进小说中,也几乎没有在书中植入自己本职工作的痕迹,甚至在小说中写到空间,比如卧室、客厅,她也并不会去描写那个空间,更不会展露出自己的建筑背景。
“我不太知道我脑子里的专业知识会体现在什么东西上,但可能会有其他的影响。”叶扬举例,《小说界》编辑沈大成曾给过她一个评价,说她小说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通常她的小说会有一个结果。很多作者会在技法、写作包括文笔上有更多的追求,但是叶扬作品是一个行为逻辑的圈,它最后会有一系列的因果关系。这可能是理工科出身的作家才有的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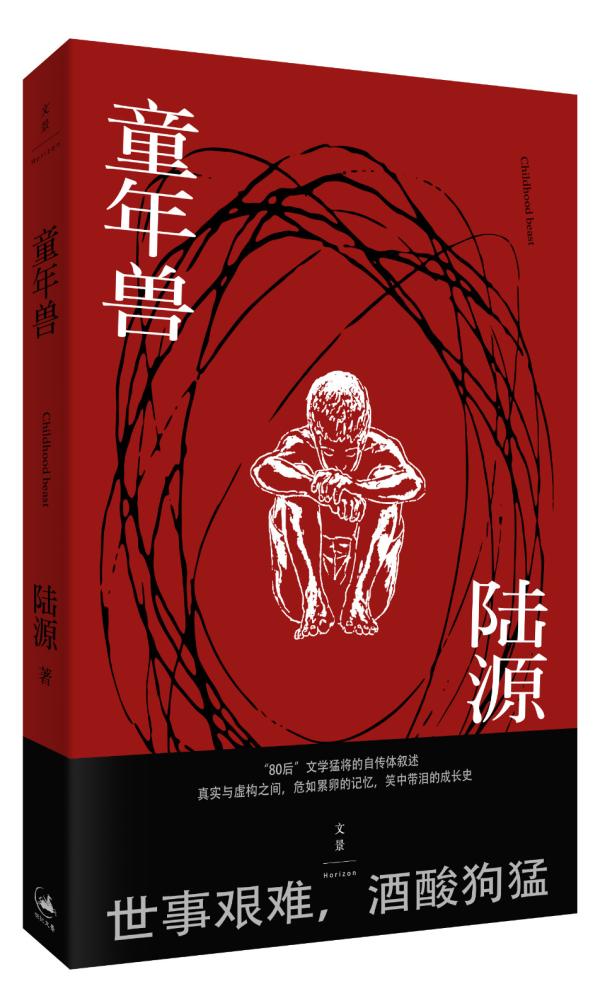
陆源的新书《童年兽》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是交织着社会历史和个人心灵史的自剖独白,而故事在一个相对特殊的空间体校围棋队展开。上世纪80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引起民间广泛关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围棋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陆源本人也成为了一名棋童,在体校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认为《童年兽》的写作是一次难以复制的过程:“到今天为止,我还不曾向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童年,将来也无须再说起。仅此一次,该说不该说的,皆已说尽。”
《童年兽》是基于陆源自身经验的半自传体小说,这跟他前两部作品完全不同,“我终于发现我的童年的这些遭遇,不是百分之百的坏事,以前的这些经历给你带来了困扰,让你难受。原来它也有可能会变成今时今日些许的成就和安慰。”
李伟长认为这意味着进步:“因为对自己的作品很平静往往是一种好的状态。我要写对的,感觉对了,情绪对了,在写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满足了自己,或者满足了一次自己,对第二次满足就没有那么期待,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陆源已经完成了一次所谓的自我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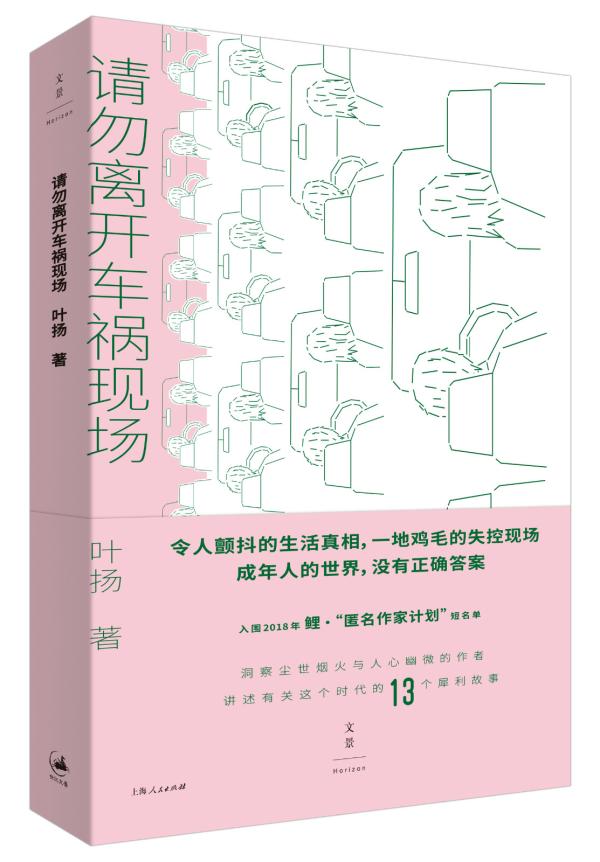
身为一个文学编辑,陆源每天都在接触大量不同年龄作者写的小说,他认为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其决定投身写作的年龄。
从这个角度讲,“80”后是幸运的,这代人在年轻时代赶上了改革开放后文学的黄金年代,在观念形成和文学训练上都正当其时,而“75”前的一代人错过了这个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80后、85后、90后我认为是成立的,有了这么一点点的机会,真的跟前面不一样。”
周嘉宁则提出另一个问题,在真正进入写作的门槛之后,随着年龄渐长,不论是什么年龄的作家,年龄的意义都会模糊,真正有价值的“是魅力本身”,是可以超越年龄,超越时代的东西。
“这个世界的舞台不分年龄,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年轻人就优待你,或者因为你是一个老年人就优待你,我觉得是特别公平的,特别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特别公平的,对于创造力和生命力是巨大的考验。”
“今天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追问自己的写作是什么样的状况。” 李伟长总结,“一个小说当它被叙述为它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那么它在这一代人的身上是有用的,但是在这一代人以后它就会消失,就会被冷落,就像我们重新去看待现当代文学里面的作品一样。”
从这个角度出发,李伟长认为,赢博体育登录一个写作者见证一个年代或者一个时代,其实还算容易,“但是如果一个写作者,它的写作能够超越10年,往下再走10年,还依然会被提起,那么他必然要具有窗口期,能反映普遍问题,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讲不应该是过时的。”(澎湃新闻记者 杨宝宝)


 发布于 2024-11-11
发布于 2024-11-11